北京疫情走了多少北漂,一场没有告别的离散
2022年的冬天,北京街头格外冷清,曾经熙熙攘攘的地铁站,排队的人群不见了;曾经灯火通明的写字楼,加班的灯光稀疏了;曾经人声鼎沸的小区,突然安静了下来,疫情三年,这座容纳了八百多万外来人口的城市,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人口迁徙,没有人统计具体数字,但每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能感受到:身边的北漂朋友,正在一个个离开。
张伟是我认识十年的北漂朋友,2013年,他带着"改变命运"的梦想从河北农村来到北京,住进了著名的"蚁族"聚集地——唐家岭,那时的唐家岭,十平米的隔断间住着六个年轻人,公共厕所永远排着长队,但每天晚上,城中村的街边摊都坐满了谈论未来的年轻人,张伟做过快递员、房产中介,最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稳定下来,月薪从三千涨到了两万,2020年疫情爆发时,他还乐观地对我说:"非典都挺过来了,这次怕什么?"然而2022年5月,连续三个月的居家办公后,公司宣布裁员50%,领完补偿金的那天晚上,张伟在电话里说:"兄弟,我准备回老家了,三十多岁,该认命了。"
像张伟这样的故事,在北京各个角落上演,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,更重塑了他们对城市的期待与忍耐,李婷是一位在国贸工作的白领,月薪三万,却住在五环外与人合租的老旧小区。"每天通勤三小时,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才发现,原来生活可以不用这么累。"2022年夏天,她辞去工作,在成都找到一份薪水略低但压力小得多的工作。"在北京十年,我一直在为户口、房子拼命,突然发现这些可能永远不属于我。"

疫情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北漂生活的脆弱性,陈默是海淀区一家教培机构的老师,月入五万,是老家父母眼中的"成功人士",2021年"双减"政策加上疫情反复,机构倒闭,34岁的他求职半年无果。"北京不相信眼泪,但眼泪早晚会流干。"今年春节后,他带着妻儿回到了郑州,用积蓄开了一家小书店。"虽然收入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,但至少晚上能睡着觉了。"
这些离开的北漂带走的不仅是他们的人生故事,还有北京的城市活力,朝阳区一家开了十五年的川菜馆老板告诉我:"以前晚上十点还满座,现在八点就没人了,很多老顾客都走了,新来的年轻人消费不起。"数据显示,2022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比2021年减少了约13万,这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大降幅。
离开的北漂中,有人是被动裁员,有人是主动选择,但共同点是他们对北京梦的重新评估,28岁的程序员王磊在离开前算了一笔账:月薪两万五,扣除房租五千、生活费四千、给家里寄三千,每月能存一万三。"看起来不少,但北京房价均价六万,我干二十年也买不起一套房。"疫情让他看清了"高薪贫困"的现实,去年他应聘了杭州一家公司,虽然工资降了15%,但公司提供人才公寓,"突然觉得生活有了盼头"。

那些仍然坚守的北漂,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与北京的关系,29岁的设计师刘悦不再执着于"一定要在北京买房"。"疫情让我明白,生活品质比房产证更重要。"她现在与人合租在朝阳公园附近,周末去郊外爬山,不再为加班牺牲全部个人时间。"如果哪天觉得不值得了,我也会离开,这没什么可耻的。"
北京疫情走了多少北漂?这个数字或许永远无法精确统计,但可以确定的是,每个离开的人都带走了一部分北京的多元与活力,而他们的离开也在重塑这座超级城市的性格,疫情像一场没有预告的考试,检验着每个异乡人与大城市的契约关系——当光环褪去,付出与回报是否仍然值得?
离去的北漂们或许会在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,或许会回到故乡寻找归属,但无论如何,他们共同谱写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为复杂的一章,这场静默的迁徙没有鲜花与告别,只有手机上一个个变更的地址和渐渐沉寂的微信群,而北京,这座习惯了人来人往的城市,会在失去与获得之间,找到新的平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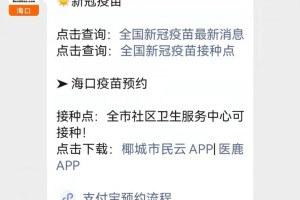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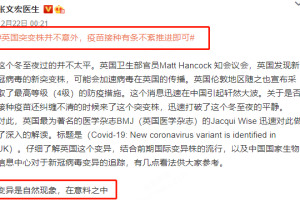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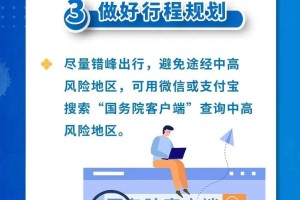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